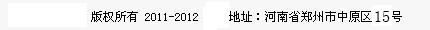西汉王朝前期的倡廉和选拔“廉吏”,一直是与褒奖三老、力田和孝悌同时运作的,且贯穿于西汉王朝的整个历史。只不过,西汉王朝中后期的民间社会推选廉吏的工作,已经被严重异化,或者是徒有其名了。因为,西汉中后期苛繁的朝廷监察职官职能制度,已在事实上不需要人民群众去监督和民主评议官员是否是“廉吏”了。由此可见,主要由老百姓去评议、选拔和监督官府官吏的民权自治的政治制度,与官方内部审查官员的监察制度,是一组彼此消长的绝对关系式!
作为政治国家,官方内部当然也还是需要监察制度的,但是,当官方内部的监察政治制度一旦过分盛大,民间社会中的民主民权制度必然会随之下降。所以,如何配置好国家社会中的民权民主制度与官方内部的监察政治制度的各自数量与权限,是国家管理官吏和防止官吏腐败的一种平衡和权衡的匹配政治关系式。
由于西汉王朝中后期的反腐与倡廉,是分离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西汉中后期,倡廉,已经沦落成为朝廷反腐监察政治机制的附属,而且,西汉王朝中后期的反腐,又充满了“人治,专权”的监察政治情况,这样的反腐,基本上可被看成是朝廷中的各政治权力和朋党势力的较量,或者可被看成为是皇权与各官僚集团权力之间的政治较量。因此,西汉王朝中后期的反腐,大多以悲剧收场,国家的正义规范及其法制,往往沦落成为了各政治帮派势力打击异己对方的工具。
汉宣帝时期的京兆尹赵广汉的个人悲剧,就充分反映了西汉王朝中后期的这种依赖“人治,权治”的监察制度去反腐的“权、法”悖论。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一带)人,生前是个出名的秉公执法者。他担任官员期间,熟知法律,执法甚严,赵广汉执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民百姓犯法,他依法处置,高官贵族犯法,他也一样依法处置,因此,他在老百姓和官场中的口碑甚好,“吏民称之不容口。长老传以为自汉兴治京兆者莫能及。”
汉宣帝时,大司马霍禹犯法,霍禹不仅仅是前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的儿子,他还是当时汉宣帝的霍皇后的亲兄弟,而京兆尹赵广汉得到举报以后,他亲自带领官吏进入霍禹府第破门搜查。前67年的汉宣帝地节三年七月,丞相魏相家庭中出了命案,丞相府第中的一个奴婢自杀死亡,传闻此奴婢是受到魏相夫人的逼迫虐待才致死的。按照西汉王朝当时已经解放奴隶和人人平等的法律制度规范,丞相府中的这件命案也应被国家司法机构所依法追究审理。
由于当时主要行政地方官员又都同时兼任司法主官,所以,作为京城长安最高长官的京兆尹赵广汉便下令自己属下调查丞相魏相家庭中的命案,但丞相魏相本人则极其不配合调查,还故意刁难赵广汉的调查程序,赵广汉为了直接取证,他只好亲自带领差役进入魏相府第且亲自审问魏相夫人,这下,就彻底得罪丞相魏相了。当时,担任朝廷监察高官的丞相司直萧望之,与魏相都属于是儒生小集团成员,他们私下为儒生朋党。
这样,中央监察高官的丞相司直萧望之不但不帮助秉公执法的赵广汉,他反而上奏汉宣帝说赵广汉上门审问丞相夫人,按照儒家上下尊卑礼法,这就是辱没大臣了。因此,这就造成不明情况的汉宣帝居然以为赵广汉过于狂妄了,结果,秉公执法的赵广汉反而被下狱治罪,魏相和萧望之等违法高官反而平安无事。这,就完全是黑白颠倒和正邪不分了。史载:“司直萧望之劾奏:“广汉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节伤化,不道。'宣帝恶之。下广汉廷尉狱。”
萧望之要求皇帝诛杀赵广汉,以维护官场中的尊卑伦理。由于种种原因,汉宣帝不得不准奏,赵广汉后被斩首示众。当这一消息被传开以后,数万吏民嚎啕大哭,他们当中许多人愿意替代赵广汉去死,因为,吏民们认为,保护了赵广汉,就可以保护更多的老百姓不被权贵家欺负。但是,赵广汉最后还是被朝廷诛杀了。赵广汉的冤死案件,典型地反映了西汉王朝中后期的国家腐败已经不可遏制的格局,也反映了朝廷监察高官们可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而凌驾于法律之上和滥用监察大权破坏正常司法的历史情况。
法律、正义和民意,甚至包括司法主官,在被霸占了政治权力、文化声望和物质财富的腐败者的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这,就是西汉王朝中后期的反腐状况,也是朝廷监察权力一旦被滥用以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当然,西汉王朝历史中,也有不少腐败官员被惩处的事例,比如,汉成帝时期的丞相匡衡贪污良田,就被朝廷惩处了。但是,即使是像匡衡这样的案件,只要我们仔细审视其被惩处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这是因为匡衡陷害忠良陈汤过于黑心,引发了朝廷大员们的众怒所致。
这就是说,如果丞相匡衡不陷害忠良陈汤,如果他不把陈汤这个跨国家作战一举消灭了匈奴郅支单于的大功臣最后陷害到边疆去当了一个戍边普通士兵,那么,也许匡衡的贪污事情,就没有那么多权贵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