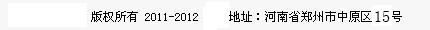一一《人面桃花》、《西厢记》、《二进宫》三剧的故事起由与发展
如果说,中华民族乃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岸骄子,华夏文化是历史天幕中的灿烂星河,那么,民族戏曲无疑是这浩瀚星河中的璀璨明珠。自古以来,在安平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上,不但孕育了兴旺发展的崭新旋律,而且产生了许许多多与戏曲有缘的人文故事。“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李艳妃做昭阳自思自想,想起了老王爷好不心伤”、“抬望眼仰天看月阑,天上人间总一般……”每每吟品这些穿透时空的醉人词调,无论在大陆、在港澳台,还是世界华人的聚集地,我们这些“黑头发、黄皮肤”的炎黄子孙,都会对祖国的传统文化肃然起敬。不为人知的是《人面桃花》《西厢记》、《二进宫》。这些剧坛佳作的故事,紧连着我的故土河北省的安平县…… (一)《人面桃花》之"崔护″与"杜宜春″(《人面桃花》剧照) 安平县在西汉时叫谷成国,西汉后期改称乐成国,后汉初年又叫安平国,至汉延喜元年改谓博陵郡,郡址先在博野县后迁安平。唐得宗李适贞元初年(公元-年),博陵人崔护(今安平县黄城人)在长安久考进士不中,独在异乡感到无聊,喝了几盅闷酒,便独自闲游走到城南庄。时值清明,桃花盛开,百草吐绿,但已日上三竿,口干身疲,见村中有一人家,便去前讨水,等了许久,有女子杜宜春自门缝问话,崔护答道:“小生博陵崔护,寻春独行,酒渴饮水。”
女子开门,端出水来,把崔护请到院内坐喝,然后斜倚在桃树旁边,深情端望“小生”,不由地绯红“浸”脸,崔护也看出姑娘俊俏知礼,顿生爱慕,喝完水起身告辞,女子却望着远去的背影,依依不舍地关门回到家中,崔护亦有留恋忘返之心……
第二年清明节,崔护进京(长安)后,急不可得故地重游待,但见门庭如故,却已上锁,人迹杳然,惆怅不已,遂在门上题诗: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人面桃花》剧照) 这首七言绝句,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诵,崔护与女子的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到明朝,临安派剧作家孟称舜,依之编成五场杂剧《桃花人面》,第一次把“崔护谒浆”搬上了戏剧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戏剧大师殴阳予倩经过再创作,完成了京剧版的《人面桃花》,尔后评剧和其他剧种纷纷改编,广为演唱,历久不衰,其中京剧名家吴素秋,评剧高手韩少云,都因扮演少女“杜宜春”名炽艺坛,其中由吴素秋参演的《人面桃花》还被拍成了京剧电影。而今,在崔护、杜宜春故事的发源地,安平人修建了人面桃花园,建设了崔护题诗旧景复原,一代又一代的博陵后人仍在传唱着"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动人旋律。
(二)《西厢记》的"莺莺″与"红娘″(《西厢记》剧照) 《西厢记》是京剧舞台上旦角行当中“张(君秋)派”艺术的经典作品,剧中德材兼备的主人公莺莺良善娴淑,冲破封建牢笼,与“君瑞”(张生)结合,虽有“红娘”牵线,但她主动追求爱情,其人其事,至今流传。(《西厢记》剧照)安平县的黄城村原叫凤凰里,莺莺乃该村人,字双文,小名莺莺,生于公元年,父亲崔元翰,名鹏(—),通晓经史诗文,年近50始举进士,唐德宗建中二年()壮元及第,在朝中言辞文雅,举止得体,但生性刚褊简傲,不能取容时政,后遭罢去官职,约66岁卒命。莺莺母亲是睦州刺史郑济之女,年生了莺莺,莺莺姨母很有文才,嫁于元氏男,年生有一子,比莺莺年长,这就是史称中唐著名诗人的元稹。莺莺父亲去世后,妻子郑氏携子女,扶夫灵柩归葬博陵墓,守孝三年后,因孤女寡母无所依靠,思虑再三,于贞元十五年,决计再回长安。途经蒲州时,正遇上“贼兵”丁文雅变,母子急忙投身河中府普寺寻避,恰遇元稹,元稹随即用计退去来犯者,救了莺莺母女,见莺莺生相俊美,顿生暧昧之情,托莺莺婢女“红娘”从中撮合,二人终在西厢结为百年之好。但后来元稹赴京赶考不归,又寻新欢,抛弃了莺莺,这个故事首先由元稹写成了《莺莺传》,也称《会真记》,很快流传开来。后代文人在此基础上创作出文学剧本,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等均为艺坛佳作;该故事也有不同的人物取向,由荀慧生先生创作的《红娘》,则重点放在了歌颂红娘的成人之美。前不久,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亲自为该剧改写了第五场,并依据人物心理,丰富和调整了部分唱段,使该剧更具魅力,在国内传为佳话。一般说来,学术界公认的是莺莺人史皆实,张生之名即为元稹之形。
不管历史如何演绎,但安平人相信文化的传承如同江河行地,必须在坚定的文化自信中发扬光大。眼下,落位于河北省安平县黄城村崔氏墓地公园的一旁,"崔莺莺大剧院″的设计、建设正在进行。
(三)《二进宫》的娘娘"李艳妃″(《二进宫》剧照) 多年以来,安平城北的南苏村有一个“村规”,无论多高规格的剧团,都不能在村里上演《二进宫》,村里的历代李姓族长已把这个“传统”延续了多年。(《二进宫》剧照) 原来,《二进宫》戏里李良太师的祖籍,是安平县的南苏村(尽管岁月更迭,村名至今未变),从李良的祖父起开始定居京城经商。李良有个漂亮女儿被选入宫中伴驾,人称李艳妃,做了娘娘后,请求回家拜祖,皇帝恩准,经过几天跋涉来到了南苏村。待到祭祖时,娘娘傻了眼,因为她一不知祖坟在哪,二不知本家是谁,急忙请来一位李姓族长遍查家谱,也未搞明“艳妃”应归哪枝哪脉?堂堂贵妃,找不到祖宗,这还得了,李娘娘眉头一挑,拉过一位老太太认了本家,故此,祭祖一事顺顺当当走了过场。
族长心想,白捡一个贵妃娘娘做族女,真乃家门有兴,世代难得!李贵妃却费了心计盘想:假如有人议论自己祖籍不真,岂不有辱当今圣上,蒙欺君之罪?于是,她决定假戏真做,越不真越要显得真切。
她求皇上修建起一条通往南苏村的“官道”,并规定:凡有南苏村李姓进京,可免费在道旁客店吃住。不久,渐有风声议起,有人传说李娘娘并不是南苏村人,不是记错了,就是听人说错了,但尽管传言不断,却没人能讲清楚。
从那以后,李娘娘一再传旨,要南苏村人进京为官,但没人敢临帝门,生怕背上冒认官亲的罪名……如今,京剧圈里“梅派”(梅兰芳流派)“张派”(张君秋流派)等都在演这出戏,不少文艺团体还把与本故事有关的“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组成连台本戏,戏报上常有“兹请名家倾艺上演《大探二》。
历史在进步的发展中,跃向高端,今天的安平县南苏村父老,也摒弃了狭隘的"李艳妃到底是不是村里人”的疑问,而对中国戏曲文化的发展充满热望。
行文至此,思绪涟涟,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传至现在,实属不易,随着时代的进步,她愈发彰显着诱人的光彩,千万不能失艺于现在,三个小剧虽为戏剧之林中的几根“薪棒”,但正是这些点点“涟漪”,已然汇成了文化“江河”,我们必须使既“源远”,更“流长”。(县文联主席王彦博供稿)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